深山里的远古战神后裔
在外人眼里,自豪地称自己为血统“最正宗的苗族”的岜沙汉子,多少有些难以言表的另类———梳着用镰刀剃成的怪异发式,一米多长的老式火枪不离身,穿着如塑料薄膜般泛着紫光的蓝靛麻布衣服,打扮极富象征意味。

世界上灾难深重而又顽强彪悍的民族中,犹太族和中国苗族的历史都是由战争和迁徙写成的,如今,遍布全球的犹太人已然是世界公民,而苗族依然在黔东南的深山里延续着对祖先传统的坚守,《苗族古歌》唱道:“奶奶离东方,队伍长又长……跋山又涉水,迁徙来西方……”从衣着、禁忌、信仰、农耕、生产、爱情……山地民族有着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倚赖,他们别无选择,自从祖先来到这里,他们的文化归宿也在此扎根、繁衍,生生不息。
一件绝对严肃而庄重的事情
岜沙的一个明显符号是“户棍”,这是在中国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男性发式,也是岜沙男人除了火枪以外最重要的标志。所谓“户棍”,就是剃掉男性头部 四周大部分的头发,仅留下头顶中部的头发并盘发为髻。岜沙男人成年之后,将终身保持这种据说是蚩尤老祖宗时代传下来的传统发式。对于岜沙的男孩来说,洗头、梳头、剪发都是绝对严肃而庄重的事情,在他们十六岁接受接受一次名为“达给”古老成人礼时,寨里的精神领袖———巫师,要用镰刀,这或许听上去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工具将他们从小留起的一头长发剃去,仅仅保留中央的一撮。据说如果外人要理这样的发式需要20元人民币,但相信除了岜沙人,没有人会愿意将自己的脑袋当麦地。
岜沙人认为树是祖先的灵魂,这些灵魂是需要被敬畏的。每一个岜沙人的出生和死亡都是祖先的灵魂在现实世界和远古世界之间的互换,是灵魂和肉体在不同时空的交替。岜沙孩子出生后,父母会为他种下一棵树,这棵树将伴随着孩子成长。如果这棵树被风刮倒或是被人砍掉,他们会认为这是非常不吉利的预兆。当一个人死去,就砍下代表他的那棵树,为他搭建起回到远古祖先那个世界的桥梁,同时在死者的墓地上栽种上另外一棵树,以示生命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开始。
执着的树木崇拜使岜沙人认为,头顶的头发就相当于树顶的树叶,树顶的叶子如果全部落光,也就表示树要死亡了。因此,头顶的发髻必须终生保留,不得损伤。完成一整套庄重的仪式之后,这留下的一撮长发将被梳成高高的发髻,终身不得改变。这种颇有秦汉时期风格的“户棍”的发式显示的是一种含蓄的雄性崇拜。
“岜沙人的枪是摘不下来的”
岜沙人深信自己是四十多个世纪前与汉族祖先黄帝争夺中原大地统治权的古代苗族、瑶族部落联盟的酋长———蚩尤大帝的后裔。他们自豪地称自己为血统“最正宗的苗族”,并认为自己的祖先是蚩尤的第三个儿子。当年蚩尤被黄帝打败,率领自己的部落向西南偏远山地迁移,岜沙人的祖先就是大迁徙的先头部队九黎部落的一支。经久的战争和迁徙使得这一支苗人对武器有着特别的渴望,他们要应对强大的华夏部落的进攻,要抵御大迁徙中遇到的猛兽,要给部落中的妇女和儿童获取动物蛋白……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岜沙村的男人依旧对火枪有着图腾般的崇拜。
十六岁,对一个岜沙男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这不仅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要接受“达给”成人礼,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背枪了,他们的父亲会亲手为他们准备好礼物———火枪,一个枪手的身份对于岜沙男人来说才意味着真正成年,可以吹芒筒、可以跳花坡、可以游方……岜沙男人的枪其实是一种老式的,射程只有二十多米的简易火药枪。在岜沙,如果能拥有祖父甚至太祖父留下来的老枪,是非常值得炫耀和自豪的事情,那是一种流淌在血液里的尚武情节,有枪在,就有勇气和力量。事实上,1949年以后,岜沙男人是被官方允许合法保留持枪传统的惟一一支少数民族部落,枪图腾对于现在的岜沙汉子来说早已不是狩猎或防身这么简单的存在意义了。“一枝猎枪一条狗,一枝扛子朝山走。”岜沙村老支书易笃培说“岜沙人的枪是摘不下来的”。直到今天,岜沙的男人们下田、看牛或上山拾柴,甚至上茅房都是依然枪不离身。
其实,岜沙村的林子里早已没有什么动物可以猎取了,更多的时候,火枪的作用如同礼炮,用来欢迎来寨子参观的游客。村民滚元亮是岜沙村的名人,确切的说,他和岜沙村都是被相机制造出来的“名人”,他的影像频繁地出现在各种媒体上,几乎成为了岜沙村的形象代言人。身高不过1米五的滚元亮目前的身份是村里的火枪表演队队长,也是最年轻的寨老。按照族里大寨老的“演义”,“滚元亮是岜沙先祖姜央的卫士转世,而岜沙男人的枪就是比照姜央的身高制作的,所以滚元亮长到1米五就再也长不上去嘞”。
岜沙村将接受一场“战争”
就在我们来到寨子的那天,他正带领着他的兄弟们在村口的芦笙坪广场上为五一长假期间来村宅游玩的客人表演“枪手舞”,狭小的村道停满了各地牌照的汽车,不伦不类的音乐在破旧且经常卡壳的录音机里弥漫开来,枪手们卖力地舞蹈赢得了不少掌声。他们被游客到处拉着合影,而岜沙人原本不愿意让外人拍照,怕把他们魂魄收进机器里被带走。考虑到游客的安全,原本朝天鸣枪的礼仪也被更换成了空枪扣扳机,“意思到了就好了嘛”,火枪队的队员腼腆地解释。寨子里多了农家旅社和农家饭店,也出现了常规旅游景点经常可以看见的小商店,出售着制作低劣的各种纪念品。古老的岜沙村不可避免地将接受一场“战争”,一场自苗族大迁徙以来的,没有硝烟和刀箭的战争,像化石一样不可再生的原生文化和传统,将不可避免地遭遇外来文明和价值观的冲击,他们被时代推上了一次精神和文化的迁徙之路。于此,我们可能无权评论什么,毕竟相机里的奇风异俗对于原住民来说也意味着沉甸甸的生活艰辛。
以前,岜沙女人的地位很低,大多没有文化,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她们甚至没办法自己收信件,留下的都是丈夫的名字。村子开发旅游后,很多女人出去打工,回来后,牛仔裤代替了传统的刺绣裙。滚元亮家的一面墙上贴的都是他的照片。他有着“非常岜沙”的外形,他去过黔东南州的首府凯里,去过首都北京,在岜沙,算是见过世面的能耐人,他把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留影贴在屋里最显眼的位置。多数时间,他要带领着村里的二十多个姑娘小伙,在芦笙坪上为游客表演拜树、“剃头”、吹芦笙、“火枪舞”……岜沙这座曾经封闭在大山深处的苗族部落必将面临着改变,当一年一度的芦笙节变成一天数次,当火枪不再需要火药触发,当传统成为经济的筹码,当世代传承的古老文化依靠纯粹而麻木的表演维系时,古老的岜沙还有多少神秘可以待价而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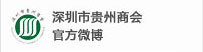



 深圳市贵州商会
深圳市贵州商会